《米纳里》:寄生虫是穷人的痛,水芹菜是穷人的乡愁
|
废气治理 http://www.voccl.com 当故乡已经陌生疏离时,我们都要在新的城市建立自己的“语言”。 《寄生虫》2020年拿下小金人之后,2021年入围奥斯卡的《米纳里》压力倍增。韩国影坛对它给予厚望,但目前看来,《米纳里》离获大奖的距离还有很远。 两部作品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。《寄生虫》是韩国人在本土的故事,而《米纳里》则是韩国人在美国的故事。两部作品最精巧的共通之处,或许只有主角的鼻子——《寄生虫》里,男主人说家里有穷人味。《米纳里》里,小男孩指着外婆,说她身上有韩国味。但讽刺的是,男主人不曾搭过地铁,小男孩也从来没去过韩国。 “米纳里”这个名字,乍一听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台湾把它翻译成《梦想之地》,过于朴素直接,更减少了观影兴趣。实际上,米纳里是韩文“미나리”的直译,意为“水芹”。东亚圈的人对这蔬菜很熟悉,长在水边,价格便宜。中医说它性寒、清热,《诗经》里写它“思乐泮水,薄采其芹”。但电影里,米纳里不只是长在无名溪边的蔬菜,它更被用来比喻亚裔移民的生存状态: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下,有水就能生长,连成片、弯着腰、对过路的人说“谢谢啦”“谢谢啦”。 电影剧照,右边的小土坡上,长的就是“米纳里” 建立语言 从本质上讲,《米纳里》只是个烂俗的西部拓荒故事。由于带着半自传色彩,它给人的感受会更加真实、动人。 片中的小孩,就仿佛导演童年的眼睛。他和姐姐、父母一起搬到具有种族歧视的美国南方小镇,住在时刻断水断电的房车里。父亲孤注一掷买下一片荒地,即使前主人曾因为这块地破产自杀,父亲也自信地认为,他能在这块地种出最好的韩国蔬菜,改善一家人的生活。 导演在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时曾说:“《米纳里》在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,这个家庭在努力学习如何说自己的语言,一个比美国语言或外国语言都更加深入的,关于心中的语言。”这段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影片的主旨:在这个小家庭里,文化差异无处不在。 父亲有拓荒的美国梦,母亲却只想攒点钱给儿子结婚;外婆从韩国带来的高价补药,在孩子心里还不如超市里的大瓶饮料;家里英文韩文混杂,小儿子说外婆不像真正的外婆(doesn't like a real grandma),外婆估计只听懂了“like”,还高兴地以为孙子喜欢他。 外婆的扮演者尹汝贞,还有一个知名综艺《尹食堂》 种种矛盾,外化成父母之间的婚姻裂痕。他们从韩国跑到美国,以为彼此可以互相拯救,但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一对纯正的韩国人,或许在当时不应该不合时宜地做着美国梦。梦很快破碎了,地里打不出水井,找不到韩国蔬菜的买家。夫妻不得不重返工厂,做小鸡性别分拣员的工作——十分直白的隐喻:有用的小母鸡放进红筐,没用的小公鸡放进白筐,等待绞碎、焚烧。 好莱坞影评人对《米纳里》的评价不高,他们认为,导演过于炫技的表达方法,让影片显得不够真诚。一如海报上写的:《米纳里》是“我们当下最需要的电影”(This is the movie we need right now)——可我们当下真正需要的东西,电影可以承载吗?他们认为,《米纳里》中移民、两性心理和东西方文化差异都提到了,可是每部分几乎平均用力,冲淡了议题背后本该有的张力,让故事陷入导演本人的私人回忆。 回忆的优势和弊端同样明显,它细腻,但也容易被矫饰。导演没有给出种种问题之下的答案,整个片子布满温柔、充满希望的基调。到收尾部分不得不给出解决方案时,天降一场大火,这个家庭被“神的旨意”团结在一起,重建了信仰和亲密关系。 在《米纳里》中,“燃烧”元素重现 如果用理性去思考,整个故事的逻辑当然不够严密,但作为观众,我还是很难不为当中的细腻、温柔、隐忍而感动。到影片最后,中风的外婆不小心点燃了农场,仓房起火,她觉得自己无用,痛苦又自责。在火光里,她颤颤巍巍地走在乡间小道上,我的眼泪唰得流了下来。片中祖孙三代女性,显然是东亚女性共有的缩影,她们对家庭的付出、对氛围变化的敏感捕捉、对自我的牺牲,甚至只是打花牌时的一点小幽默,都很容易让人充满共情。 影片最后,男主人公蹲在溪边,打理、采摘外婆留下的“米纳里”。此时,水芹已连成片,互相缠绕着,像杂草一样,覆盖一片被荒废的土地。 一千个观众,有一千种对“米纳里”的解读。它的意义是流动的,时而只是溪边的野菜,时而能代表身在北美的东亚移民不屈不挠的精神,时而代表着让自己变得有用的“社达”主义,时而又是属于韩国人甚至整个东亚圈的文化漫游...... 《米纳里》剧照 但在那一刻,我突然感受到自己也是“米纳里”。那是一种身处一线城市,却依然逃不脱传统文化和小镇泥土的乡愁。当故乡已经陌生疏离时,我们都要在新的城市建立自己的“语言”。 “驶”向奥斯卡 除了“水芹”的意象,值得留意的是,在今年的颁奖季影片中,主人公大多不住在传统的住宅里,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。 《米纳里》一家人睡在农场旁的移动板房里,很容易停水,没有垃圾处理站。片中有很多镜头,是在刻画生活条件的恶劣,例如他们只能把生活垃圾扔进铁桶里焚烧,龙卷风一来,全家人都得坐在电视前关注天气,并时刻准备发动汽车“逃命”。 《米纳里》一家人居住的地方 与之相似的,还有《无依之地》和《金属之声》。前者的背景设置在金融危机后,数百工人为了生存,以旅行车和面包车为介质,随着临时工作季节性迁徙、搭建临时社区。后者的主角是摇滚乐队的鼓手,因为经济状况捉襟见肘,不得不住在房车里,四处漂泊寻找演出机会。 无论是移动板房还是房车,其实都具备生活条件,只是缺少“稳定”的概念。作者凭借这样的住所,得以刻画边缘人物在广阔自然环境下的状态以及内心的孤独。 电影学者王小鲁在评价《无依之地》时曾说,房车生活是一种反对陈旧资本主义体系的新生活模式。资本主义系统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,而房车生活正是对此的一种反抗。 《无依之地》的主角住在房车里 《米纳里》一家人主动从韩国移民美国,从大城市搬到乡下,其实也是在逃离固有的社会秩序。母亲带着家人坐车去做礼拜,在“正常的社区”里显得格格不入。而父亲不想一辈子对着小鸡屁股,宁愿花光家里的积蓄也要开垦韩国农场,这与东亚传统意义中“买房买车、成家立业”的愿望背道而驰。 但可惜的是,《米纳里》只描述了父母作为一代移民的生活现状,似乎无意做更多阐释。这或许正是私人回忆的缺点:整部影片被处理得诗意、浪漫,一笔带过了移民生活的黑暗和辛苦,似乎是想给处境不幸的父母留下某种尊严。 影片结尾没有给出大火后,来之不易的订单被烧毁,一家人将如何重新生活的答案。我们可以想象,一代移民终其一生可能都是两种文化的“外来者”。就像住在移动板房里的《米纳里》一家人,既无法得到传统住宅的安稳,又不像“房车一族”一样拥有真正的自由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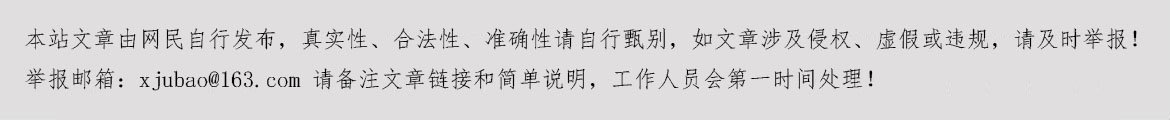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

